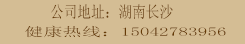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肾病医院 > 治疗肾病 > 年2期周凌张万桑南京鼓楼医
当前位置: 肾病医院 > 治疗肾病 > 年2期周凌张万桑南京鼓楼医

![]() 当前位置: 肾病医院 > 治疗肾病 > 年2期周凌张万桑南京鼓楼医
当前位置: 肾病医院 > 治疗肾病 > 年2期周凌张万桑南京鼓楼医
周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张万桑瑞士Lemanarc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
对谈时间:年10月11日
对谈地点:医院
(本文原载于《建筑学报》年2期,如转载须注明出处)
承载身体的建筑与容纳灵魂的花园
——关于医院南扩工程的对谈
文字整理/殷强周青吴黎明
医院全景
医院方案的形成,概念以及设计过程
周凌南大与医院只有一墙之隔,我在校园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也去使用过几次,看病或者看病人。它给人的印象是:空间开阔、干净整齐、不拥挤不排队,一切井井有条。流线安排非常合理,标识系统也很清晰,病人少走很多冤枉路。除了时尚的外表、现代的空间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功能很好用,医院类型的一个重要作品。请您介绍一下医院方案的概念形成及设计过程。
张万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整个医院方案的过程很说明设计的互动性。最早我们在国际竞标过程中提出了一些观点。
“医疗的院落”是一件事,“医院”来自于中文“医疗的院落”的概念,它跟西医的“hospital”不一样,“hospital”是聚集以治疗的意思,和“hospice”意思接近。中国人的概念,医者是围绕着病患走的,我们在整个生病的全程,都是以一种被护理的方式存在,所以它集中反映在“医疗的院落”的“医疗”两个字上,英文叫“healinggarden”。这个概念在西方也逐渐被接受,比如瑞士巴医院新楼,就受到很多医院的模组化作法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东方文化身份色彩的。
北庭院
第二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是在一个万人口的医院,它是拥有1张病床、每天1万人门诊量的庞然大物,坐落于一块狭长的4万多㎡的场地上。基于这么高的容积率要求,按照习惯性的现代主义规划学的理解,就是楼要高,底下交通面积放出来,所谓叫“给予公众”。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不对,因为这样的理解造成地面只是一个大菜场一样,跟医院一样,底下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只有把界面严格地切出来,先划定在这个城市中,医院,医院,在这以后,才能在各方面让它纯净下来。如果静不下来,首先医院,也就是这个边界若不切出来,我就没有办法给自己倒腾出一个安静的区域来,这个很像我们现代主义对城市的理解,当城市的边界被消灭的时候,城市的一切美好的意义都被消灭了。年深圳双年展也在讨论这个“边界”“边缘”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作为一个城市中心的重量级体块,它的边界如果不是被清晰界定的话,或者不敢于被清晰界定的话,医院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把它的边界部分在地块允许的可能性下最大化地切出来。在这个情况下,我如何让它做得低?因为做得越低,今后的竖向交通越容易做。
医院南广场
第三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是,这个地块是天津路和中山路交界的一个狭长形地块。天津路正平行于明朝南京鼓楼的轴线,而中山路呢,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民国首都的“十”字规划中南北向的一条。整个场所处在明朝和民国两个时代的夹角,那我该怎么做?是我做完之后,明朝也不要了?民国也不要了?我又创新了?还是我让这城市留下点什么记忆?
我的应对方式就是把这体块转化:北部的体块,也就是住院部和医技部,它的张力源于鼓楼,依循于天津路轴线;从南部来的体块,也就是门诊部就依循于中山路轴线。这两个体块得到以后就交错起来了。为什么这么交错呢?我觉得一个呢,是呼应前两个事物,它的确记住了历史上的这两个轴线,轴线是需要实体载体来记忆它记载它的;第二,它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有趣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在天津路看到有个屋盖的地方,中山路的一个双层平台和花园,没这交角还出不来,北部的空间也没有办法和1号楼形成一个安静的北广场。
西南鸟瞰效果
关于“医院”一词的理解
周凌您之前说到的“hospital”的起源,跟“hotel”和“hospice”接近,其实这些词都来自中世纪拉丁文“hospes”,里面有“避难”“休闲”“招待”的意思。医院对于医院和医学的理解还是不太一样。年前,加拿大的马林医生建立了医院,他带来的不仅是西医的技术,还有他作为医院和医学的理解。我们平时来这里也觉得医院医院不太一样,很多医生会耐心向病人讲解病理,医院创始人马林医生建立的医疗文化有关系?
(注:医院创建于年,最早为美国教会的加拿大籍医学博士威廉姆·爱德华·麦克林WilliamE.Macklin医院“医院”,年改为金陵大学医院,是南京医院。年,医院成为南医院。)
张万桑医疗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医疗”,远远不只是治疗你身体的问题,马林当时就讲过一句话:“华佗之功救人身体,圣灵之力拯人灵魂”。
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好几年前骑摩托车摔倒了,胸口砸在一块石头上,疼得不行,感觉快死了,去医院,一拍片子说没事,当场就不疼了。60%的病是和心理有关系的,所以,“healthcare”很大程度上是心理问题。我们对于治疗这件事情是基于信仰的,首先,你信仰你能否被治疗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这种信任和信仰能帮助你治疗。医疗完全是人类行为和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医疗这件事情,完全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一个科技现象,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就有一个承载的源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hospice”一样。
医院是很典型的两个文化的相遇,是西方人医院,又被东方化了,为中国人服务,这已经超级混乱了,文化身份已经混淆到不知怎么去界定了,有没有一点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共同点还是在这个“garden”上面。
西方人提到的人之初是“伊甸园”,东方人古代的理想,也是园。它的尺度,可以大到皇家苑囿,也可以小到阳台窗前的一个小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但归结起来都是一个字“园”。“园”是我们心灵的归所,医院,这个23万㎡的庞然大物,就应该是来承载“园”的,所以就有了3个层级的“园”:6个大的庭院,还有30多个采光井,以及表皮上无数的小“园”,因为病人躺在里面,没办法去外面看大的“园”,“园”得贴近人,否则毫无意义。
从北至南的6个庭院
像周老师在做的成都赭石门会所里面,也是一个外部界定,里面去造“园”,大家都在“园”这个方面探索。医院,在市中心一个功能如此重要的建筑里面,我们依然应该把心灵的居所“园”作为第一位去承载。如果说建筑物承载着身体的话,那么花园则承载着我们的灵魂。
关于医院功能和流线的问题
周凌请您介绍下医院功能和流线处理。
医院是各类建筑类型里面,功能最复杂的。医院,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医院长相基本上都是水平的线条。因为水平线最容易处理:条窗、层间带、设备。医院的模数非常讲究。医院里面的空间每一年都在不断变化,所以怎医院做到flexible,做到“柔性”?我们选用了一个跟中国现在的医疗模数比较匹配的模数:1.3m。在中国,比较中等的、经济的方式,用地指标大概在一张病床㎡,1.3m的模数相对它的使用率,比较紧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现在医院的住院病区是一个环形,这样一个环形病区在中国几乎是唯一的,医院有3种分类方式:一是以介入与否分为大内、大外、康复等;二是按照人的身体系统来分类,像脑科、眼科等;三是以收治的时间来分的,如住院、门诊、急诊等。这3种分类方式,如何在空间矩阵上最有效最有利的相互接近?无论是上下还是左右,都是能抓得住,找得着的,包括它们的物流系统。超有意思,这是一道很复杂的算术题!
周凌这个“回”字形为什么可以做到?
张万桑首先呢,“回”字形,是由4个“L”形组成的,每个基本单元是一个“L”形,因为要满足模数化的建造。一个护士站,在中国现状下的经济做法,最好是管两个unit,叫“双病区”。本来是一个“双病区”的一个楼加另一个“双病区”的楼,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说10层是心脏科,就会出现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医生共用问题就产生了,这就造成了医生在跨越病区的时候要先下到下面再绕回到10层。而这个方式(“回”字形)解决了任何一个点的工作人员可以同时水平向或竖向最快到达目的地的问题。
周凌所以病人也能很快地到达目的地,比如做支架的,属于心脏内科,做搭桥手术的,属于心脏外科,病情不确定时他经常需要两边跑,实际上是双向的,两种选择,两个通道,最近距离搭在一起。
张万桑对!所以它由之前的两个双护理单元,变成现在的双倍的双护理单元,以及内部还是双通道的状态,非常高效,从“双核”发展到了“四核”的住院部。环回带来的问题是,大约有20来个病房是朝北的,但是从整体性上来说,病人住院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这一部分朝北的房间,换来的效率是很可观的,所以后来也没有人再去诟病这个问题了。这个最终闭合的医院管理者的认真互动是分不开的,让我和我的团队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医患汇流原理
周凌每层的挂号和取药是当时您提出来的还是院方的要求?
张万桑这个是我们提出来的。在中国,这可能是第一个以系统化的严谨的医疗矩医院。在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地下一层在急诊区的下面是药品中心及所有手术的supply区域,为什么选择放在这里,不放在门诊?因为如果放在门诊,它只能直达门诊,不能直达住院,也不能直达急诊,当门诊、急诊、住院都需要药品的时候,物理上就应该是自下而上垂直到达的,所以几个葫芦串交合的点的区域就很重要,就在它下面。所以,1万人的门诊量,取药、化验,平常要跑多少路,现在只要在本层就可以解决,而且每层都在同一个区域,非常方便,减少了很多内部无意义的流动。
周凌这个特别重要,就跟中国城市一样,很多的路是没有必要的,中国小区的环路,很多都是浪费的。国外,像我们之前和欧洲规划师合作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设计,基地内有很多小山脉,他们首先把适宜建设的区域划出来,确定一条主干道以后,其他支路就一支一支地伸进山凹里去,没有像国内校园一定要有内环外环。
反思我们中国做的很多校园或居住区方案,包括城市规划,都是一环,二环,三环,其实三环以后的外环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那些支端的连接都是浪费的,效率特别低。医院在流线和路径设计方面确实做到了非常高效。包括一些垂直的药品流线,三维方向上整合了患者、医生和药品的关系。
关于对城市的理解,医院和城市的问题,都市主义或者现代主义?
周凌在城市方面,医院的做法是延续鼓楼的轴线加上中山路的轴线,相交成交角,在医院的形体上体现出来。但是另外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都市主义的做法,类似于医院旁边的紫峰大厦建筑群,建筑师也很重视鼓楼这个历史遗存,紫峰的几个体积,最终都是通过轴线来打穿鼓楼的轴线,包括景观和中庭都是对在鼓楼这个视觉通廊上。它的方法比较美国式,先把城市边界占满,地块是三角形就是三角形体块占满,不强调建筑内部的自主性。医院我觉得可能有点体现欧洲大陆思想上的一些特点:建筑形体自身是完形,然后通过完形的内部单元的组合变化,去适应城市边界。紫峰更强调都市主义,它不管建筑内部柱网不规则的问题,但是要守住城市边界。我觉得你们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张万桑对,我的想法是要守住城市边界的同时又不希望它等于城市的规划边界,还是希望一些accident(有趣的偶发)能创造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周凌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代主义体积的观点,特别是瑞士人,我的理解是:瑞士山地较多,自然环境更美,不少建筑师,如博塔他们都喜欢使用大体积矩形,更多强调体积本身的东西,不是那么都市性,而反之商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就会把边界都用齐。另一个就是,可能欧洲人对于自我系统的理解,像德国、瑞士,是一种自足的,从内到外的整体性,必然是方盒子最好。像你的模数,如果形体是斜的,可能模数就贯彻不了。同时满足了这两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都市主义,跟美国人那种不强调最终的逻辑关系的实用主义不同,我一直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建筑师处理建筑体块和城市关系的态度。
张万桑我们采用这个模数,核心问题来源于医疗功能空间的使用率和它的柔性变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模数既要满足门诊,又要满足住院病房,还得满足医技部的医学仪器的使用设置,同时还要设想在今后的岁月里面,医院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功能置换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里面有三角或者异形的空间,医院改变起来就很难,而且涉及到设备系统的整合,难度就很大了。
周凌功能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张万桑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我来看,东方人气质里面的基础是方正的、直的,在没有一个特殊原因改变它的方向之前,它是不会动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承载一个原因,会被读解出来,会有一层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也和你之前说的瑞士的极简主义,非常理性的思维是比较接近的。
关于城市的问题,就像您之前提到的,我认为有几条线索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是当西医文化和中国文化相遇以后,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他们的共同语言或者说共同语境是什么?最后提炼出来的是“园”,花园作为心灵的居所被承载;第二个呢,从基督教的意义上讲,又有一层含义。可能我们中国人不是特别了解,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对于西医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西方的中世纪,西医全部存在于教会、传教士和修道院,修道院掌握着所有的科学技术,现在的ICU就是典型的修道院布置,两边摆床,医生护士在中间走,这和在教堂里面摆床是一样的。
我当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建筑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信任和信仰?我想帮助重建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所以,对于基督教的感受,我是想传达出来的。比如说内庭,就是现在的“钢琴厅”,是想让它有很纯净很安静的感觉,有点像教堂一样,你看两边的挑台,可能让我们想起教堂里的唱诗班站的地方,顶上一个个射灯的管有点像管风琴。就是想让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礼拜堂的感受。
教堂般的住院部内庭
还有,医院理解成一个孤岛,为什么建筑表皮在周边都要拉开一个距离并落下去?当然一个是帮助地下室的逃生、采光和雨水,还有一个就是想让这个建筑物和不属于这个建筑物的闹市很清晰地区别开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建筑物与城市好像不是一回事?
医院岛
周凌有点悬浮在城市中的感觉,能看出建筑师的意图来。就像密斯的西格拉姆大厦一样,也是很纯净地把它隔离开来,前面用两个水池,故意设计得不能让人坐,只能站一会就走了,跟外界环境完全隔离开来,很有仪式感。
张万桑对,我就是想用这种仪式感来把它孤岛化,因为它本身就应该是岛,为什么提到“岛”这个概念?可能我需要解释一下,医院,医院叫IslandHospital。病人心理上就认定这里是一个神圣的属于此岸和彼岸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都病了,还得混在城市里面,还不能得到一个和上帝更近距离修养的机会,都觉得白病了一场。之前提到以现代设计的方法,来实现我们中国人能感受到的文化身份,但是它这个文化身份又不是西方的,它有着非常浓厚的东方情结,西方人造个房子,外围弄个狩猎场,他的“园”是开敞的,中国人是到了“园”里才算回家了,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文化身份。
庭院芦苇塘中的静思
关于医院的材料、建造和立面
周凌医院的立面很有趣,单元设计很复杂,一层层的layer,以至于看了好几遍才能记住它的构造关系,有什么道理吗?造价是不是很贵?
仰视立面花园
立面花园的厚度
张万桑那时候我记得网上有批判说“医院”,其实它们真的是没有。医院造下来的最终的结算造价是元/㎡——原来是元/㎡,后来全部杂七杂八,就是包括景观全部,是元/㎡。元/㎡是什么概念?它是中国这个时期里几乎是最便宜医院——就是土建安装全加起来,包括立面,包括家具。
周凌立面是整体的是吧?
张万桑是单元式幕墙。它每一个单元的中分隔之间是mm,所以我们室内方案每一道隔道的分线全部都是对应的,但是到了国内的施工配合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周凌柱网也是?
张万桑对,柱网中心线是7,的6倍。整个医院是由标准的诊疗单元的模块组成的。一个unit大致的面积在㎡,基本是一个空调的分区,乘以4是防火分区,它全部是模数化,所有的家具也全部是模数化。使用6倍模数和你设计的南大教学楼(费彝民楼)有相似的地方。
模块化临床单元
这个建筑的表皮是3层组成的,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凹窗、一个凸窗,再加一个悬挂外面的纱网。大家远看的时候纱网和凸窗基本混合在一起,所以这种漂浮的边界(overlap)可以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光,医院的主要朝向是东西向,两幢楼绵延多米,如果不做处理,两边基本是东西向,西晒。凸窗这部分让光在一天从早到晚都很敏感,就像传统的画室,要么朝北,要么有弥散光。受这个启发,做了最外这个磨砂的玻璃。这个窗子是双层夹胶玻璃,有2道、4个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单元式幕墙,凹窗管景,凸窗管光,侧窗管风。
立面解析
中间的这个区域是MiniPocketGarden(微型口袋花园),每个房间都拥有它,我们做了预制的植物架子,在两边的杆上挂上去,用以色列的滴管技术培育。但是最后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安装。之所以要做这个MiniPocketGarden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房间都能感受到这个小花园。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对我来说,建筑是花园的载体,并不是说我们造了建筑,旁边再要去找一个花园,建筑的目的就是花园,人类最美好的初始,伊甸园,也是garden。所以我想用这个建筑试着讲这么一句话:建筑是花园的载体。
还有sunshading(遮阳),这个体积进行了大面积的遮阳,让东西向最大的直晒区域的阳光被屏蔽掉了。所以我们测算下来的节能应该是很好的,据大家反映也是很好的。但是最后要靠数据来讲话。我们现在还停留在测算和信心层面上。
外墙大样
周凌有没有通风和节能试验?这个玻璃有什么特殊的处理?在镀膜节能上有专门的处理吗?
张万桑试验就是要靠年底数据。如果就节能系数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这一个单元平均的U值(传热系数)是在1.7,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概念了。凸窗的玻璃是有两块玻璃夹胶,外面这层是钢化玻璃,就是钢化夹胶1号面磨砂玻璃。所以它碎掉以后不会掉下来,只会软掉。因为它本身的弥散光,镀膜节能在这个上面就不需要了。在凹窗里面是有一层Low-E的镀膜。
这层立面建造完的总体的造价是/㎡。它为什么这个价格就能做下来呢?因为标准化、模数化的设计。它全部是单元式的,工厂里生产好,现场装配。大家知道在中国的现状,职业的自律也好,现场施工的控制也好,如果你不走工厂预制的路,这么大规模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当时设计了工厂预制的单元式幕墙。
周凌像那个立面单元在当时实施的时候,院方有没有什么不理解和阻力?
张万桑当时的阻力还是非常大的,说实话,有点一意孤行。在我办公室的小花园里,有个架子上放满了立面的小样,用来研究玻璃、孔网、磨砂玻璃和铝塑扣板这4个材料的构造和组合方式。4种材料中迎向外立面的有3个:玻璃、孔网和磨砂玻璃,他们的通透度,也就是透明度、遮光度这几个数据,铝合金厂商和玻璃厂商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连计算的仪器也不一致,根本协调不起来。我把他们各个厂商的人叫到一起,告诉我各自通透率的算法,我给他们现场算算术,现场协调各个数据。最后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几层像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最外面一层材料,在概念设计的时候应该是一道玻璃,是磨砂玻璃外面又有一道磨砂玻璃,但是我要是用两道磨砂玻璃,它的重量和费用都会增大,所以我必须把最外面一层置换为孔网。但是我如何做到孔网和磨砂玻璃的质感在一定距离外是基本一致的?光是这一点,在我小花园里,小样就有6次,每天早上拍,中午拍,晚上拍,1:1的大样也做了6次。最后大家才看到像是几张纸这么一叠的效果,看起来很轻柔,什么都没有似的。什么都没有其实是最难的,你得让它们看起来一致,但是它们本来不一致。有些事情,只有建筑师一意孤行地去做,去控制,才能到达想要的效果。这样的感受太深了,建筑师就要有超强的神经,要能坚持到底。
病房窗景
明亮的病房(摄影:陈尚辉)
一层平面
二层平面
标准层平面
工程档案
设计单位瑞士Lemanarc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
建筑师张万桑
地点/江苏南京
设计/年/竣工/年
业主医院
基地面积3.3h㎡
建筑面积23万㎡
结构形式钢筋混凝土框架+框架剪力墙
摄影夏强(除标注外)
(本文为节选,原载于《建筑学报》年2期,如转载须注明出处,欢迎订购纸刊及iPad完整版查阅全文,欢迎点击右上角分享:)
————————————
感谢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engshis.com/sbzl/156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