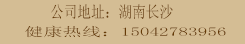肾病二科(三)
好像还真应了老头子的闺女的那句话:这是个诞生奇迹的时代。三天之后,老头子差不多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坐起来了!他开始要吃要喝,嘴巴里不停地在咀嚼,发出呱唧呱唧的声响,让旁人听着都觉得难堪,很不文雅,很不舒服。而他自己呢,好似浑然无觉,或者说毫不在意,自顾自地大吃大嚼,津津有味,那架势,仿佛一个荒野逃生回来的流浪汉,一头扎进了家里的厨房,翻箱倒柜,无所不爱。他吃得汁水横流,沥沥啦啦地滴答在胸脯的外衣上,像个初学吃饭的婴幼儿,嘴角沾满了泡沫状的唾液和食物的糊状渣滓,脸上挂着痴迷的微笑。他闺女无可奈何,给他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充当临时性的“围嘴儿”,隔一会儿就要用纸巾给他揩拭嘴巴,擦掉那些不雅的咀嚼残留物。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她对2号病床的郊县夫妇说,“我这个老爸啊,胃口好大,像头大象。”
“不像大象,”2号病友的老婆说,“像头老牛,会反刍,能倒嚼。”
“别管像什么吧,”老头子的闺女说,“反正能说明他胃口好,身体正在迅速地康复。”
老头子特别爱吃黄瓜。他闺女把黄瓜削了皮,他接过来握在手里,咔嚓咔嚓地塞进嘴里大嚼。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他闺女说。
那根黄瓜像一截甘蔗握在手里,没过一会儿就缩短了。
病房里回荡着黄瓜破碎的声响,牙齿摩擦的声响,舌头吞咽的声响,甚至还能听到唾液和胃液上下会合、漫延流动的那种细微声响,窸窸窣窣,纠纠缠缠。
“再来一根。”老头子开始能说话了。他的词汇量和他的食量在同比例增长。
“不行!”闺女说,“爱吃什么就没个够?适可而止,知不知道?”
“她没事吧?你妈。”老头子开始操闲心了。
“没事?可能吗?”他闺女说,“半个小时前,我给她收拾利落,从五楼下来的,这不,刚洗了手,你就要吃黄瓜。”
“你确实洗手了吗?”
“洗了洗了洗了!”
“又怎么了,她?又跟昨天一样?”
“你说我容易吗?四楼五楼,跑上跑下,又是爹又是妈,这个需要挖屎,那个需要把尿,这个贪吃,那个任性。”
“又拉裤子里了?”
“爸,你说她是不是成心的,故意的,是不是不给我找这种臭麻烦就不甘心?”她拍打着自己已经日渐干瘪下垂的胸脯,怨恼地说。
“唉,一辈子要样子,她。”
“那就落下个这样子?她!”
事实上,老婆子是有一个便携式坐便器的。那个物件的外形,类似于一把电镀折叠椅子,坐面上有一个椭圆形凹洞,凹洞下连着一个塑料大抽斗,承装汇集排泄物。完事后,将抽斗抽拉出来,端到卫生间里倒掉,清洗干净了,再插回坐便器原位。老婆子只要自己褪了裤子坐上去,麻烦问题便能解决了,可要命的是,她死活不肯坐上去;这么说也不太准确,事实上是,她曾坐上去那么一两次,体验过,以后便死活再也不肯坐上去了。她说坐到那上面,拉尿时声响大,丢人现眼,排泄得不痛快,不彻底,不舒坦。她要上厕所,上卫生间,像个正常人一样蹲在便坑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有人随时伺候着,搀扶着她挪进卫生间,拉拽着她小心翼翼地蹲到便坑上,完事后,还要帮她擦抹干净,抽水冲刷。谁来干这个差事?当然是她闺女,这好像别无二选。义不容辞,合情合理,就因为她是她闺女。老婆子一有了便意,就会按响电铃,把五楼的护士传唤过来,五楼的护士是不会帮她完成这项低级事情的,这不是重症监护室,她们不承担这桩义务,她们用内部传声电话通知四楼的护理站,四楼护理站的护士再把这个讯息传递给老婆子的闺女:
“五楼,你妈要解手,赶紧上去吧!”
在病房,被传唤时,老婆子的闺女可能正在做瑜伽,或者可能正在侍弄老头子,或者可能正在与2号病友的老婆闲扯,或者可能正在准备一顿饭菜……总之,不管正在干什么,她都要麻利地应承一句:
“好的,这就上去!”
要是每次都这样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会有特殊情况。那就是:闺女还没来得及跑上五楼,老婆子已经拉尿在裤裆里了。她毕竟老了,越来越搂不住火了,大脑越来越控制不住下属的各个器官和组织系统了,在闺女没有出现之前,她就肆意妄为了,任其发泄了,图了个一时痛快,弄了个满屋恶臭。
“造孽啊!看你这副出息劲儿。”
她给她收拾。把她按在病床上,戴上口罩,扒下她的裤子,隔着卫生纸去抓粘糊在裤裆上的那些属于这个世界上的最脏的东西,就那么一把一把地抓下来,扔进一个塑料袋子里。一边抓,一边还要不住地给同病房的其他病友和家属道歉:
“真对不起,对不起啊,给你们带害了!”
其他病友和家属基本上都不搭腔,眼睛尽量不朝她们那个方向转,活动稍微方便点的,干脆捂着鼻子躲了出去,实在没办法的,只能强忍着,强忍着侵袭而来的挥发性臭气,强忍着满腔愤怒和怨气。那些咒骂和指责就堵在牙齿缝儿里,只差一点儿就要喷溅出来了,上下两片嘴唇抿了抿,硬是给包扎了回去。
努把劲儿,压一压吧,唉,这是在哪儿?医院。医院是个什么地方?万般无奈地去所;但凡有点奈何,哪个愿意住进这里?
“实在是对不住啊!”老婆子的闺女说,始终红着一张脸,脖颈和耳朵都感觉到热辣辣的,“我这个老妈就是这样,我行我素,自我得很,一辈子了,我们这些个做子女的,能咋地?哎呀,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她觍着脸说着这些讨好的话,尽力给自己找回些面子,而不争气的是,手里正撕扯着一大块儿即将投入使用的卫生纸。
“谁没个老的时候?”这间病房里一个上了年纪的病友说,“受罪呀,活着就这么回事。”
这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话,既是对老婆子的闺女说,算是对她的歉意的回应,也是对病房里的其他病友和家属说,算是为她的困窘解围。
就在那个特定时刻,那个老婆子,她的老妈,呜呜地哭泣起来。哭得那么难听,哭得那么艰难,就像有一枚滚动的核桃卡在她的嗓子眼儿里了似的。
起初,她被她闺女按在病床上扒裤子的时候,她始终在嘿嘿嘿地发出怪笑,同时还一呼一吸地呻吟着,好像在暗示她闺女,在刚刚炮制的那场排泄事故当中,自己用去了多么大的体力似的。她闺女每擦抹一下她的老屁股,她就故意痉挛一下,非常夸张的一种反应。这是一张怎样衰败的老屁股啊,弹性彻底丧失,沟渠和皱纹五花八门,几朵黑雀斑像干枯的昆虫标本附着其间,通体蒸腾着热烘烘的酸臭和腐败。她闺女一边擦抹着,脑子里偶尔会无端地冒出一种冲动:要张开指甲去抓扯它、揪挠它,抠挖它。因为在她沉重的感官空间里,它和一团陈年糟朽的烂棉絮毫无二致,早该翻新了,找个弹棉花的工匠,嘣嘣嘣地弹起来,弹起来,让那根能崩碎棉花的弓弦,发出它强有力的震颤——嘣嘣嘣,噌噌噌……
可是,现在,她忽然又哭泣起来了。
“哭什么?受委屈了,你还?”
“不要忘了,”老婆子趴在那里,断断断续地说,“不要忘了,你不要忘了,你也是从我手里,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
“是啊,您说得对!”她闺女说,“现在,我不是正在给您还债吗?”
“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没有我,你自己拉出的屎,就能够活埋了你;你自己尿下的尿,就能够淹没了你。你不要忘了!”
“是啊,您说得对!这话您要是能够早点告诉我,我还真想那时就让自己的屎给活埋了,让自己的尿给淹没了,一了百了,干净利索,也省下现在还得给您挖屎?尿,偿还这笔陈年旧债。”
外面起风了。几个塑料袋子随风飘舞起来,在半空中横冲直撞了几个来回后,径直贴到了树枝上,传出凌乱的泼剌剌的脆响。透过窗户纱窗,干燥的风灌了进来,像一波又一波海浪一样,盘旋片刻,又崩溃消散。在这个空当,病房的气味改变了一些,一种清爽干练的味道,让房间里的人都悄悄地吃了一惊。
每扇窗户外面的墙壁立面上,都安装着一个承载空调的三角铁架子,那些聪明机智的病人家属们,不约而同地,都把这块犄角旮旯的小小空间给巧妙地利用了起来,变成了各自天然的保鲜储藏柜。蔬菜水果,真空包装的即食食品,密封的奶制品,超市采买回来的速冻半成品,都能别出心裁地码放在那里,整齐而严密,井然而有序;如果有人站在楼下的那片小停车场上朝楼上望去,不经意间会发现,病房的那一整面墙壁,真是五彩缤纷,花花绿绿,燃烧着一种杂乱无章的盎然生机。这是一面典型的塑料袋子和硬纸盒子组合而成的“装饰墙”,每个低廉的塑料袋子和硬纸盒子,都在无声地宣告着:无论是深层次的化学工业时代,还是高密度的机械化大制造时代,窗户里面每张病床上的病人们,都能很好地适应下来,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理由以及低成本的方式,继续把生命顽强地延续下去;他们不能不吃,不能不喝,不能不无比地留恋着这个世界。
2号病友的老婆走到窗台前,拉开纱窗,探出她滚圆的肥身子,整理自家的那些塑料袋子和硬纸盒子。之后,她顺手合住了玻璃窗子。这属于一个习惯性的举动,完全是下意识的,外面起风了,她就把窗户合住,免得室内吹进沙尘。
尽管如此,仅仅是玻璃窗户的一开一合,整个楼道里那种尿液的氨气味道,以及一种根本无法辨识成分的酸腻气流,便立即回涌而来,阴暗的,浓重的,房间里像是漫延开来一条无形的冰河,迅速侵溺了每个鼻孔,一种不寒而栗的承受感,往复徘徊。事实上,那正是死神身上的气味。
“哎呀,”正在地板上铺着的棉线毯子上做瑜伽动作的老头子的闺女喊道,“快把窗户打开吧!——差点儿憋死我了。”
“哎呀,是啊,是啊。”2号病友的老婆赶紧再次打开了玻璃窗户,“开着窗户一点也不觉得,一合住,没想到有这么强烈。”
“哎呀,都是风造的怪。”老头子的闺女说,“风没进来之前,我们在屋子里待习惯了,没觉出气味有什么不对;风进来后,我们可算吸了几口新鲜气儿;刚尝到个甜头,窗户被你猛地一合,糟了,又回到旧社会了。”
“哎呀,你可是啥也知道!风是个咋回事,你也分析得头头是道。”
“哎呀,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对劲儿啊——你家的那个沉默的老公哪去了?”
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正式提出来的。
是的,2号病友突然不见了,消失了。
也就是几分钟之前吧,他还端坐在病床上,两只大手杵着床铺,和屁股一起坚定地支撑着自己的整个身体。他的脖子向正前方斜伸着,和那张大脸庞配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套汽车方向盘的标准造型。他呆呆地凝望着窗外,那副老和尚入定般的痴迷表情,就好像在注视着风的盘旋轨迹,谛听着室外各种纷杂的天籁回响,就好像神思天外,超然忘我,好不淡定!而事实上,这些空明的思想境界和他丝毫不沾边际,那时,他心里正燃烧着一把火,意念中,脚踩虚拟的离合器,手握前进的方向盘,只差一个最后决断,他便要点火启动,然后风驰电掣。
“哎呀,他肯定是去厕所了,”2号病友的老婆说,“过一会儿就会回来。”
“哎呀,可还是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啊——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啊。”老头子的闺女说,“你帮我回想一下,他刚才还好好地坐在那儿,”她指了一下2号病友的老婆背后的那张2号病床,“可就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不见了。他是怎么从这个病房的门出去的,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呢?”
“哎呀,你别一惊一乍的。刚才你不是尽顾着讨论风和窗户的问题嘛!”
“哎呀,真不对劲儿啊,你自己快去厕所看看吧!”
“哎呀,快快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哇,少操别人家的闲心。”
“哎呀,我真没别的意思,你别误会我。”
“哎呀,知道你一片好心!他十点半还要去做透析,他个人接济着自己的事情了,他又不是个傻子。”
事实上,老头子的闺女的第六感觉真的很接近一个女巫。她的判断相当犀利,这真的有点可怕,没人能说清是个什么道理;现代心理学上有种过敏型人格的说法,其特征和表现不知道是不是和她有某些类似的地方。
2号病友失踪了。失踪的确切时间,就是那阵风刮起来的时候。
而在此之前的一两天,1号病床的老头子已经能够自主下地,并且能够在病房里踟蹰而行了。为此,洪主任进来例行查房时,曾高度表扬过他:
“恢复得真是不错。老爷子,我们都看好你呦,一定要继续加油噢!”
尽管如此,但是眼下,洪主任却是没有一点心情和精力再去北京中科白颠疯医院白癜风吃什么药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engshis.com/sbmb/3498.html